|
孙原&彭禹:力量来自思想的自由

明天
孙原和彭禹自毕业后一直以“合作者”身份出现在各种创作和展览中。在1990年代末他们创作的《连体》成为2000年左右“对伤害迷恋”的代表作之一。但当人们有些武断地这样定义他们的创作的时候,恰恰忽略了其中的关于“反抗”的巧妙构思,可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与当时艺术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19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现实的基调是“调侃”和“反讽”,艺术的自我价值通过“毁损”带来普遍关注。新的力量和价值如何通过创造性而得以显现?当时一些年轻艺术家开始以自己的创作和行动提出行动方案。孙原和彭禹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蜜》展出于邱志杰策划的“后感性:异性与妄想”(1999年),《连体》则展出于栗宪庭策划的“对伤害的迷恋”(2000年)中,这两件作品及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期间参加由艾未未和冯博一共同策划的外围展“不合作态度”的《独居动物》和《追杀灵魂》,由于使用当时惊世骇俗的材料来探讨生与死、肉体与灵魂等问题,引起了现场惊骇、不适和恐慌的效果;体验的观念在他们的创作一直处于重要的位置,他们的创作中经常运用活的动物和事件性因素,使其作品充满偶发性的现场感和不稳定性张力。他们以科学、冷静精神在此后不断运用摄影、录像、装置、表演等方式进行艺术“挑战”。
2000年后,他们将思考关涉社会禁区规则、艺术改变的权利等问题上,《犬勿近》中对狗的奔跑训练(2003年)、《安全岛》中老虎的威慑和《争霸》中人的对抗等,着力于对控制我们的有形和无形力量的关注,将社会通行的人类法则以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隐喻社会倡导的竞争中隐藏的对抗性矛盾的现实境遇。
当人们由于他们过于外观化的效果和冲击力而忽略了其内在的思考时,他们创作了《老人院》、《明天》、《天使》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仍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但其中的思考显得成熟起来,力量也更加内敛和集中。将展出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现场的《一时清醒》这件对生存状态提问和思考的作品,将科学与试验、动力机制与美学追求结合出意外的叙事感,与2009年6月展出于唐人画廊的《自由》一起,成为这两位艺术家近期引起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创作。
徐震:在艺术体制中反思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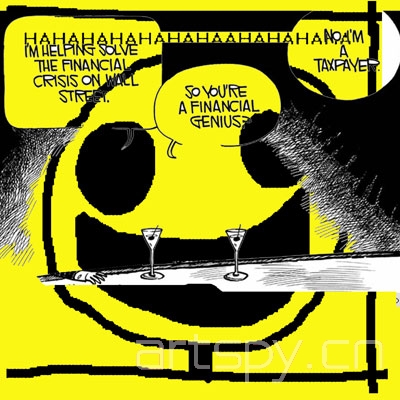
蔓延 B-012
“我觉得艺术家可以做任何事情,不再是仅仅表现美的画家,不再只是固定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感受,包括挑战常人的常识、心理底线和道德禁忌。这种挑战,其意义就在于可以让大家换一种方式看问题。” 徐震在中国艺术界也是一位集艺术家、独立艺术空间总监、艺术网站创始人等身份于一身的人。
1999年,他和多位艺术家在上海共同策划了著名的当代艺术展“超市”,随后的一年,他加入了比翼艺术中心,成为了该中心的艺术总监,组织策划了很多大型年轻艺术家群展。1990年代末期,徐震以一系列从不同角度关涉身体与身体的界限的作品引起注意。对人的身体的关注,对生理的题材的强调,将一种青春期躁动暧昧的内在体验,一种微观的身体政治与对现实的体认关联起来,作品中有一种犀利调侃的力量和挑战权威的反叛和挑衅欲望。
他的系列装置和项目却带有一种明显的行动性,2005年参加“横滨三年展”的代表作《8848-1. 86》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节点,在作品里,徐震用录像、照片等证明具有世界第一高峰之称的珠穆朗玛峰被他锯掉了1.86米(这相当于他的身高),他开始以事件而不是作品的形式引起媒体对其作品的关注。他认为:“媒体的反映本身就是一种材料。由于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对许多‘世界第一’、‘之最’等纪录有依赖感。能否摆脱这种依赖?以当时的判断,至少有人会相信,但没人能去证实。这正是该作品的讨巧之处。”2008年11月在长征空间的个展“可能性第一”中展示的两件作品,也针对新闻真实和评判标准,他以创作中体系的界面刷新,对当代艺术创作的过程及当代中国艺术和所谓的国际的关系提出疑问,提出新的“价值协商点”,并以种种可能性引起艺术界的讨论。
自2009年9月开始,“徐震”时代结束,“Made in”时代开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不仅仅是在以后创作的作品上换一个署名,也不是艺术家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带来的创造活力,“Made in”意味着艺术创作是可以是股份制实体的方式进行运作的,可以进行知识产权的买卖和组织艺术生产而成为一个品牌型的艺术计划。但徐震也说:“Made in会与年青艺术家合作,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风格可以很多样。”放弃署名权意味着对于作者权利的放弃,这对于盛行于西方的著作权利体系而言,是一个挑战,而对于中国的“盗版”现实也是一种拷问;同时,也是对艺术权利的一种提问。作者权利意味着什么?原创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创新来说,一个“股份制”的艺术创作机制会带来什么样的创造活力或者问题?徐震的尝试同样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和受关注性,他在此也成为一个示范者。
郑国谷:艺术正在创造的多重可能

帝国感应篇
“‘帝国时代’电脑游戏那里没有烧烤,我的帝国有。”这句话有着典型的郑国谷风格,一种将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置于生存价值的内在性之中,并存有一种随缘的松动。从2004年,郑国谷在阳江城郊从买了一片近一万平方米的土地开始,创造他的“帝国时代”,现在,这个项目正在慢慢演化成他用生命和生活构筑的艺术项目。他在与作家和策划人的胡昉的谈话中说道:“《帝国》是一个时代,总会消失,但它保留了从违章到合法的印记,政府的各种部门的公关、国土局、规划设计院等等,始终会保留的。”他也将自己的计划称为“新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帝国计划”是从最初对生活理想的构思到生活的设计的变化的见证。
胡昉曾在《在家的周围活动》一文,描绘了郑国谷(及阳江青年)的生活:“一个海边小岛,一个年轻的暴力中心,一个受暴力旋涡波及的陆地边缘,依然有恐惧和欢乐,职业和对抗,家庭的乐趣和琐碎的装修思想,这里有游戏,也有真实的微笑——年岁越长,笑得越真。”郑国谷自毕业后就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家乡——广东的一个小城市阳江,这里与南中国的很多中小城市一样,在1990年后逐步变成发展和消费景观所带动的社会景观的缩影。
在1990年代中期,郑国谷创作了有影响的作品,如反映受到光怪陆离的香港消费文化影响而构建的阳江青年的生活理想系列之一“阳江青年生活”(1996—1997)、“一个青年男子的新娘理想”(1995—1999)系列等。对于郑国谷来说,力量是流动的,很像“借力打力”这句中国民间语言,生活中任何的启发时刻都可以是他开始创作的源头,向生活的现场借力,使他的作品有着草根的力度。凭借生活赐予的力量和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他在阳江创造了几乎独一无二的当代艺术,作品的容量也变得很大,似乎边界全无。这种“个人化景观”是否是对艺术各种规则的有意冒犯?
在阳江,郑国谷和他的伙伴们发展出一个很有地方形象的“文人”圈子,他们是这个城市的艺术家、建筑师、音乐人、出版人和诗人,等等,作为有个性、独特、位于边缘却朝气勃勃、充满自信的文化,他们似乎在反对一切墨守成规和规定成型的关于生活抑或是艺术的见解,也许,这是越来越有意思和张力的、无论是关于艺术还是关于生活的着力构思,新的世界就也许将出现在不同世界交会的地方。
杨福东:艺术中的思想机制 如何形成

离信之雾(剧照)
杨福东在他十多年的工作中,用自己独创的语言和创作方式拓展了艺术叙事的多重可能性,他用繁杂的符号和散漫的结构来消解艺术创作中的单一的叙事线索和结构,试图制造出复杂性、慢速和间断的时间叙事。在他的电影作品中弥漫着不确定的场景,不确定的人物,突兀的道具,如同《浦东第一个知识分子》(2000年)困惑的位置感和期待。“矛盾”、“不确定性”、“疏离感”这些杨福东关注的词汇在不经意间撩拨起观众的注意。
杨福东历经五年拍摄电影《竹林七贤》(2003—2007),作品借用魏晋时代著名的“竹林七贤”的故事,勾连当下生活中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绪。以“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的独特魅力,是发现了自己的内心情怀,可以欢愉,可以忧伤,狂放不羁,率真洒脱。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风度”在这里隐喻青年知识分子珍重自我、追求精神自由的情怀,以及对“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语)精神的观照,“竹林七贤”成为对青年人向往在精神上远离真实世界,寻求自我空间的一种描绘,也是对身处现实的慨叹。
这次展出的《离信之雾》是杨福东2009年完成的,由9个35毫米黑白电影组成的影像装置。在这件作品中,每个电影都设置了一个场景,每个场景都是由重复拍摄的镜头组成,其中有些镜头被认为是“成功的”,也有许多是“不成功的”,这些镜头一并被剪辑在电影中。9台电影放映机同时播出9个画面,使这部作品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电影观看方式,观众可以在9台电影机和9个屏幕之间自由选择,放映机的“机器之美”和屏幕上的内容一起呈现给观众。
“我把它称是‘行进中的电影’,有点像把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作电影来做。在我看来,它一方面是部(多屏)电影,另一方面又具有来自电影机本身的装置的感觉。” 杨福东这个作品不仅是改变了电影的观看方式和对电影结构固有的理解,也是对电影机“权利”和对电影中时间控制的解放。当观众不必被电影的内容结构限制而具有了观看主动和选择权利时,电影的叙事结构和时间性也随之改变了,观众的自行编辑,个别经验的加入和个人体验的自由联想,在平展的画面处形成褶皱,形成不同断层并形成深度。
杨福东多年创作中一直构想的以电影构筑一种思想的画面和思想的机制的实验,有了重要的进展——这个重要的转变始于杨福东2008年参加“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的作品《青?麒麟》。假如电影中的画面是表现理念的符号,《青?麒麟》及《离信之雾》中多重现实材料的堆积和拥塞,使一种基础的、源自生活的、宝藏的“地质学”开始形成,“这两年,我确实对很多事情、人、物以及状态有一定的思考和看法。自己会产生新的感觉,身上有种看不见的责任感,对社会的思考确实存在……” 杨福东开始从一个风格化的、具有自我创作品位的“实验电影作者”,向以纪实的角度凝视社会内部,以一种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和体认,作为面对思想危机和艺术思考视点的艺术家转变。
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将要展开。
——汉娜·阿伦特
创新性因素是一切革命所固有的。“中坚: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八个关键形象”在展览中比较集中地呈现这些年轻艺术家的思想动机和创作状态,我们可以在其中观察到他们对于现实的体认和理解,他们创设的问题界面及在解决问题时的思想机制;展览也意在讨论在今天的现实中,艺术家如何思考被称为“艺术”的事情,他们所构思的关于“知识分子”及“介入”社会的主张,如何能在当下的艺术实践中被焕发出新的精神感受?中国艺术家如何在“本土”和“国际”这个长期困扰着艺术创作的语境中,从艺术史、艺术界的影响的惯性中,实现一种创新的可能性?艺术家面临的新的精神境况和现实,也使他们在思考用新的思考方式、新的问题界面和艺术生产方式,来实现一种艺术面貌的更新。中国当代艺术是否真正进入了如大家所期待的又一个新的转型期?也许,这也是我们在展览中要提出的问题。
感谢UCCA提供资料
|